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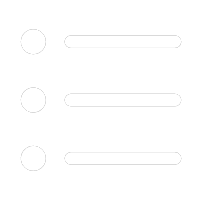


慧产科技集团
官方公众号

招商洞察
招商热点精准洞察

慧立方
聚智慧、立产业、兴地方
2008年,合肥市政府正面临一个足以影响未来数十年命运的抉择:是否拿出全年财政收入的80%投入京东方六代线项目?彼时液晶显示产业被外资垄断,一条生产线动辄百亿的投资让金融机构望而却步,投还是不投?——投!
正是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,开启了合肥从“三线城市”到“产业高地”的逆袭之路。这座被誉为“最牛风投城市”的地方,凭借以基金为核心的资本招商模式,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GDP突破万亿、跻身“新一线城市”,更完成从“家电之都”到“显示重镇、IC之都、新能源汽车之城”的华丽蝶变。
一、合肥产业发展的破局与升级
合肥的产业崛起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从“政策招商”到“资本招商”的关键转型,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城市能级与产业竞争力的跃升。
(一)1.0:筑牢产业根基
21世纪初,合肥依托“给政策、给资源”的传统招商模式,率先在家电与光伏两大领域形成产业集群。在家电产业领域,合肥凭借区位与成本优势,吸引美的、海尔、格力、惠而浦等头部企业落户,逐步建成“中国家电产业基地”。合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3年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、彩电“四大件”产量达6461.03万台,同比增长12.4%,其中冰箱、洗衣机产量均创历史新高,分别达2382.37万台、2688.62万台;核心零部件压缩机、电机产能超3000万台,其市场份额连续7年居全国之首。
在光伏产业领域,合肥以“打造光伏应用第一城”为目标,集聚阳光电源(全球光伏逆变器龙头)、通威、晶澳等企业,构建起完整产业链。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:土地、税收优惠等资源投入易陷入“同质化竞争”;对技术密集、资金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力有限,合肥亟需更适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招商模式。
(二)2.0:“无中生有”育新业
2005年,合肥正式迈入“资本招商”时代。以政府基金为核心工具,通过股权投资带动重大项目落地,逐步形成“芯屏汽合”(芯片、新型显示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)+“急终生智”(应急与公共安全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智能终端)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格局。
新型显示产业:通过投资京东方6代线、8.5代线、10.5代线(全球首条),累计投入超1000亿元,形成“从沙子到整机”的全产业链。2024年该产业产值达1235.35亿元,同比增长21.5%,2025年前两月继续保持26.3%的高速增长,产业集群综合排名居全国首位。京东方在合肥已形成“1+4+N+生态链”业务架构,其LCD液晶面板在整体及5大主流应用市场的出货量和出货面积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首位。
集成电路产业:依托长鑫存储、晶合集成等龙头项目,吸引联发科等300余家企业落户。其中长鑫存储内存芯片项目总投资达1500亿元,由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合作启动,合肥市出资75%,兆易创新出资25%,填补了国内DRAM存储器芯片量产的“卡脖子”空白。
新能源汽车产业:通过战略投资蔚来、江淮等企业,集聚120余家上下游企业,形成完整产业链,入选国家首批“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”。2020年蔚来因补贴退坡陷入危机时,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注资70亿元助其渡过难关,如今已见证蔚来年销超9万台(如2024年)的奇迹。
资本招商的成效直接反映在城市综合实力上:2020年合肥GDP首次突破万亿,达10045.7亿元;2010-2020年十年间GDP增幅达272%,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次于贵阳;城市能级从“三线”跃升至“新一线”,完成了“量级”与“质量”的双重跨越。
二、合肥市以政府资本进行基金操盘的内在逻辑
合肥资本招商的核心,是构建了一套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政府基金体系。与社会资本不同,合肥政府基金以“产业培育”为核心目标,兼具“撬动资源、引导方向、耐心陪伴”三大特质,在市场失灵领域精准补位。
(一)政府基金的三大核心特质
撬动:集中力量办大事
战略性新兴产业多为“重资产、长周期”领域,单个项目投资规模动辄百亿级。合肥政府基金通过“财政出资+社会资本募集”模式攻克重大项目:京东方10.5代线总投资400亿元,合肥财政出资180亿元并协调贷款撬动社会资本;长鑫存储总投资1500亿元,通过引入国家大基金等社会资本确保项目落地。合肥对京东方的“豪赌”,直接拉动了本地投资,加速了招商项目落户,提升了合肥在国内的战略地位。
引导:锚定产业主攻方向
合肥政府基金紧扣“芯屏汽合”等主导产业,引导资本向“投早、投小、投新”倾斜。针对早期科技企业设立天使基金,对成长成熟期企业通过母基金参股社会子基金,约定“返投本地”比例。如2022年联合新站区设立9亿元新站产业基金,6个月内投资15个项目,精准覆盖新型显示、集成电路产业链。
耐心:与企业同甘共苦
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迭代快、市场不确定性高。合肥政府基金对投资回报、退出周期具有更高包容度:2022年昆山恒美光电因调试世界首条2.5米宽幅偏光片产线陷入资金困境,合肥及长丰县合计投资5700万美元,半年后企业实现盈利并随即在长丰投资20亿元建设PMMA膜材生产基地;对蔚来的投资从2020年危机时刻持续至今,陪伴企业从股价跌至1美元濒临退市到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。
(二)“两头配置,中间引导”的基金定位
合肥政府基金聚焦“早期项目”与“重大项目”两大市场失灵领域,对成长成熟期项目以引导为主,形成精准定位。
早期项目:育种育苗破难题
通过政策体系支撑、天使基金操盘和制度创新护航三大举措破解早期科技企业融资难。合肥市天使投资基金规模居安徽首位,风险容忍度达40%,为全国最高水平;60%投资项目成立不满2年,85%为企业首轮投资。全国率先提出“尽职免责”制度,在尽调充分、程序合规前提下,投资损失不追究管理人责任,同时“让渡收益”——项目成功则将股权增值收益让渡给创业团队。
重大项目:抓住“牛鼻子”带集群
通过“直接投资+配套支持”招引龙头项目:累计向京东方系列项目投资超1000亿元,带动玻璃基板、偏光片、驱动芯片等配套企业落户,形成千亿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;投资长鑫存储建成国内首条DRAM量产线,带动沛顿科技(存储封测)、鑫丰科技(配套材料)等上下游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。
成长成熟期:引导社会资本参与
通过“做LP”放大资本效应,设立100亿元创投引导基金和200亿元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;通过“做GP”主动布局产业,截至2022年底打造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“基金丛林”,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1600亿元,带动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。
三、合肥在基金投资方面模式创新
合肥政府基金通过创新投资模式,确保“资金投在合肥、项目落在合肥、产业兴在合肥”,探索出覆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与迁移需求的五大投资路径。
(一)投资外地公司,推动总部迁址
针对一线城市溢出的优质企业,通过股权投资换取总部及上市主体迁址。如车载无线充电龙头有感科技获合肥投促基金领投8000万元、高新区跟投2000万元后,将总部从外地迁址合肥高新区,不仅带来核心技术,还带动车载无线充电产业链配套企业集聚;专注汽车AR-HUD的疆程科技获投1000万元后从深圳迁址合肥,填补了本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空白。
(二)反向吸收合并,确立合肥总部
对“外地母公司+合肥子公司”架构企业,投资子公司推动其反向吸收合并母公司。全球最大硅基OLED厂商视涯科技2017年落户合肥时总部在上海,2018年初合肥产投通过新站产业基金一期出资5000万元参与总部设立,后又通过二期基金投资2亿元确保项目推进,同时协调本地金融机构提供贷款、融资租赁等服务。2019年企业按约定完成反向合并,合肥公司成为总部及上市主体,建成全球首条专注于12吋晶圆的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生产线,具备每月9000片12吋晶圆投片的加工能力。
(三)分拆上市公司业务,落地合肥
针对上市公司拟独立发展的优质业务,投资推动分拆至合肥设立新公司。信创龙头卓怡恒通原为供应链上市公司怡亚通的子公司,2019年合肥产投与怡亚通磋商,推动其从上市公司剥离并迁址合肥,投资建设年产70万台国产计算机主板项目,2020年即实现盈利,成为国内信创主板领域的核心企业。
(四)投资母公司,撬动返投合肥
对总部难搬迁的外地母公司,通过投资换取其在合肥设生产/研发基地。昆山恒美光电在获得合肥投资后,不仅自身盈利,更带动产业链延伸;北京六分科技、泰瑞数创等企业在合肥投资后,均在合肥设立子公司,布局车联网、数字孪生等赛道。
(五)设立合资公司,加速项目落地
针对母公司投资流程复杂情况,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确保资金与项目落地。OLED材料龙头鼎材科技与合肥投促基金合作设立合资公司,建设量产基地为合肥维信诺生产线配套,成为国内唯一实现高世代线彩色光刻胶量产的本土企业,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。
四、合肥资本招商的九大成功经验
合肥以基金助力产业发展的成功,基于对产业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市场逻辑的尊重,沉淀出九大核心经验:
超前谋划:立足自身科教资源(中科大、中科院研究院所)与产业基础,提前布局长周期赛道。2008年投资京东方时国内显示产业尚处起步阶段,2016年投资长鑫存储时DRAM仍被国外企业垄断,正是这种“超前布局”让合肥在产业爆发期占据先机。
顶层规划:坚持“顶格推进、一任接着一任干”,从京东方到长鑫存储再到蔚来,多届政府持续投入不因换届而改变方向;明确“招引龙头—龙头牵引—产业配套—产业链布局—产业集聚”的清晰路径。
创新机制:通过“40%风险容忍”“尽职免责”“收益让渡”等制度设计,打消“不敢投、不愿投”的顾虑。正如合肥产投团队在尽调长鑫存储项目时展现的专业判断:“技术路线虽有风险,但值得一搏”。
精准选标:不唯“贵”而唯“适”,既投资京东方、长鑫存储等行业龙头“锦上添花”,更在企业低谷期“雪中送炭”(如蔚来、恒美光电),以合理成本获取产业资源。
专业运作:打造“懂产业、通资本”的专业团队,用“定增+债转股”等市场化工具实现政策性目标。对京东方采用的投资组合工具、对长鑫存储引入国家大基金的风险共担模式,均体现专业化运作水准。
差异定位:聚焦早期与重大项目,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成熟期项目,形成“政府补位、市场主导”格局,确保财政资金用在“刀刃上”。
长期陪伴:投资京东方16年(2008-2024)、长鑫存储8年、蔚来5年,以“耐心资本”陪伴企业跨越周期,这种长期主义是产业扎根的关键。
协同联动:通过“基金+基地”“投资+招商”模式实现市区两级联动,市级平台负责专业投资、产业研判,县区负责政策配套、落地服务,形成“1+1>2”的招商合力。
循环发展:通过上市、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,形成“投资-退出-再投资”的良性循环。京东方6代线、8.5代线项目在完成投资退出时,合肥获得的收益约200亿元;长鑫存储B轮融资估值达750亿元,合肥产投股权大幅增值。
五、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后的一些个人思考
2024年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的正式施行与2025年国办1号文的出台,标志着中国招商引资进入“后优惠时代”。条例明确禁止无依据的税收优惠、差异化财政补贴,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》则要求破除地方保护主义,而《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更是直指“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”,鼓励取消注册地限制和返投比例要求。在传统优惠政策退场的背景下,合肥以基金为核心的产业培育模式如何适配新政要求,成为地方政府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。
(一)政策合规性重构
新政下的基金招商首先需要完成合规性重塑。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堵住了选择性补贴、定向优惠等传统招商路径,而国办1号文则明确政府投资基金应聚焦“重大战略、重点领域和市场力量难以触及的薄弱环节”,这与合肥早期通过基金培育京东方、长鑫存储等“卡脖子”项目的实践高度契合。合肥模式的可借鉴之处在于:其基金投资始终以产业价值创造为核心,而非简单的项目搬运——京东方项目带动形成从玻璃基板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,长鑫存储则填补国内DRAM量产空白,这种“硬科技+全链条”的投资逻辑完全符合新政鼓励的“培育新质生产力”导向。
合规性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“去行政化”的基金运作机制。合肥通过“母基金+专业子基金”架构实现政企分离:市级母基金负责战略方向把控,具体投资决策由市场化团队执行,这种模式既避免了行政干预,又能确保资金投向符合产业规划。广东的实践进一步证明,将基金投资纳入招商引资绩效评价而非直接考核项目数量,能有效规避政策套利风险,这与国办1号文“发挥基金功能性作用”的要求一脉相承。
(二)合肥范式的进化
面对“取消注册地限制及返投比例”的新政要求,合肥模式需要从三个维度实现进化:
产业逻辑升级方面,合肥早期对京东方的投资虽带有“绑定本地生产”的诉求,但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产业链构建。在新政背景下,这种逻辑可升级为“全国性产业链布局中的节点竞争”。正如国办1号文所强调的,政府投资基金应“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及科技创新,举全国之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”。合肥可依托现有显示、集成电路等产业优势,通过基金参与全国性产业链投资,在开放协作中巩固自身节点地位,而非固守本地闭环。
运作机制创新上,合肥原有的“返投比例”约束需转向“产业生态贡献度”评估。可借鉴浙江新昌县的“基金+飞地”模式,在北上广深设立基金支点,通过投资全国优质项目反哺本地产业升级。新昌40亿元规模的基金通过“直投+基金”双轮联动,仅2024年就获得14个项目推荐,其中2个总投资12亿元的项目成功落地,这种“跳出本地招项目”的思路完全契合统一大市场要求。合肥的经验表明,基金招商的核心价值在于“以资本为纽带整合全国资源”,而非简单要求企业在本地设厂。
退出循环优化方面,合肥早年通过上市退出实现收益再投资的做法,在新政下更具示范意义。国办1号文鼓励“规范基金退出机制”,合肥可探索S基金(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)模式,通过转让存量股权实现资金回笼。合肥市共创接力基金已尝试认购苏州上实盛世园丰S基金份额,这种“存量盘活”方式既能提高资金周转率,又符合“全国资本流动”的政策导向。
(三)差异化适配策略
不同城市在新政下需根据自身禀赋调整基金招商策略,合肥经验的适配性呈现明显梯度特征:
省级政府应承担起区域基金统筹职责。国办1号文明确“省级政府要统筹管理本地区政府投资基金”,防止重复建设。可借鉴合肥“基金丛林”模式,建立覆盖早期、成长期的基金矩阵,但需避免同质化竞争。安徽省通过省级母基金联动各地市子基金的做法值得推广,既发挥了合肥的产业判断优势,又带动了皖北、皖西等地的产业协同发展,形成“核心引领+多点支撑”的区域格局。
地级市需聚焦“产业链深耕”而非规模扩张。对于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市,可参考合肥投资长鑫存储的“补链强链”逻辑,围绕1-2个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基金。广东某地级市通过国企收购上市公司、将并购企业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的做法,既规避了直接补贴的合规风险,又实现了产业升级目标,这种“股权运作替代政策优惠”的思路具有普适性。但需注意控制基金规模,避免超越财政承受能力。
县级政府则应严守“严控新设基金”的政策红线。财政薄弱地区可借鉴共青城基金小镇的“轻资产服务模式”,通过提供注册便利、财税服务等配套,吸引基金管理人落户,以服务收益替代直接出资风险。共青城集聚6600多家投资机构的实践证明,没有强财政实力也能通过“基金生态服务”获得发展红利。对于确有出资能力的县区,应严格执行“提级审批”制度,避免盲目跟风设立产业基金。
财政薄弱地区的破局之道在于“轻量化起步+风险共担”。可设立1亿元-5000万元规模的种子基金,聚焦大学生创业、乡土人才项目等本地特色领域,参照合肥40%的风险容忍度设置合理容错机制。更关键的是引入“双GP”模式,与头部创投机构合作,由专业机构负责项目筛选,政府侧重政策配套,既降低投资风险,又符合“专业人做专业事”的新政精神。
(四)转型关键支撑
新政下基金招商的成功,最终依赖于系统性能力建设。从合肥及各地实践来看,需要构建三大支撑体系:
专业化运作机制是核心保障。合肥产投“懂产业、通资本”的团队特质,在新政下更显珍贵。国办1号文强调“发挥专业管理人作用”,地方政府应通过市场化招聘组建基金管理团队,建立“跟投机制”和“收益让渡”制度。产业链服务能力决定招商质量。新政下的招商竞争已从“政策优惠”转向“生态优势”,地方政府需围绕基金投资的项目,提供技术研发、市场对接、人才配套等增值服务。跨区域协同网络是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。合肥可联合长三角城市发起“产业链基金联盟”,围绕集成电路、新能源等领域开展联合投资,既放大资本声量,又避免重复建设。这种“基金+产业”的区域协作模式,既符合国办1号文“举全国之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”的要求,也能为地方政府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赢得发展空间。
从合肥的实践来看,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非限制基金招商的“紧箍咒”,而是推动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“指挥棒”。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,是将合肥经验中的“产业判断能力”“资本运作能力”“生态构建能力”与新政要求相结合,从“政策优惠比拼”转向“价值创造竞争”。无论是大城市的“基金丛林”、中小城市的“生态招商”,还是财政薄弱地区的“服务赋能”,都需要把握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专业运作、风险可控”的基本原则,这正是合肥模式在新政下的核心启示。